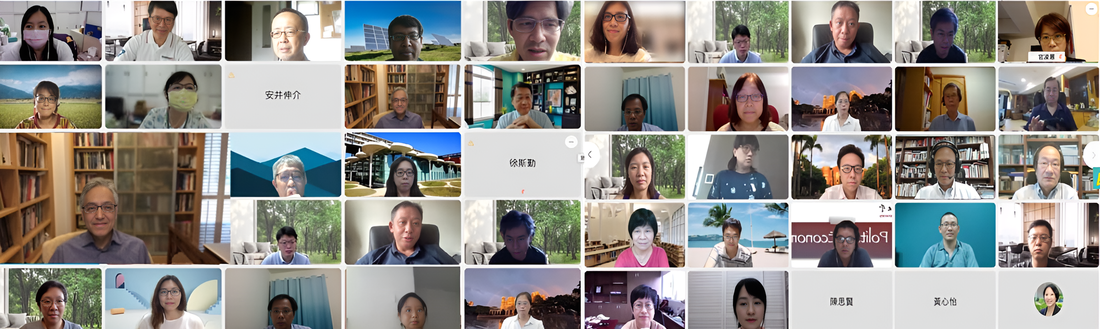|
憶雲漢兄
驟聞雲漢兄不幸仙逝,何其意外與悲痛! 他的離去,是國內及國際政治學界的重大損失。 他對東亞政治經濟、國際政治經濟、兩岸關係及民主化的研究成果,以及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貢獻,均產生重大及深遠的影響。 在我擔任台大社會科學院院長及台大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期間,他正擔任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在他長期的支持下,台大社科院與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以及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等兩岸著名高校研究院,從2012年起共同開設兩岸社會科學暑期高級講習班,每年有30位兩岸社會科學博士生、博士後年輕學者,以及相關領域研究學者參與,分別在兩岸隔年辦理,對兩岸年輕學者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具有深遠的影響。 感念雲漢兄對台灣政治學、人文社會科學,乃至東亞、兩岸政經發展的遠見與貢獻。 藉此敬表最大敬意與最深懷念之意。 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 趙永茂 聽到朱雲漢教授過世消息,相當震驚與難過!
雲漢兄是我台大政治系多年同事,是典型的學術取向傑出知識份子,曾共同在研討會中相互切磋,一起出書,並曾在我草創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時協助蓄積研究能量。 凡此共同走過的痕跡,對我而言均點滴在心!斯人故去,除為國家社會感到惋惜之外,也感慨士林痛失英才!而其全球化論述及對蔣經國紀念園區的貢獻,也將長留去思。 如今雲漢兄追隨其一生最欽仰的恩師胡佛教授而去,益發予人典型在夙昔的追思與懷念! 包宗和 朱雲漢教授是我四十多年的至友,從1977年起,我們就開始合作編書,翻譯,寫文章,探索中國現代化之路與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軌跡。我們也有幸在胡佛老師的指導與照顧下,親炙儒家傳統的師徒身教,也體會到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知識傳承結合下的涵容開闊丶博大精深。
就在他辭世之前的幾天,我們還就胡佛教授遺集的出版做最後的安排。雲漢兄的細心丶周到丶真誠,努力不懈,是讓人欽佩與感動的。他的學術成就舉世矚目,他的人格光輝與道德文章,更足為學界之楷模! 雲漢教授千古。 In Lieu of a Eulogy: My Take on (朱雲漢) Yun-han Chu’s Bigger Picture By: Chih-yu Shih (also available at https://youtu.be/NvA0ME2u8ps)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only one rarely noticed characteristic of Yun-han, one that even his beloved teacher, Professor Hu Fu, might have not detected. Specifically, Yun-han would never engage in fruitless debating to clarify confusion or calumny if the conditions did not appear ready for such engagement. This is a little like Confucius, who advised temporary retirement from public life during periods of chaos. This characteristic alludes to an intellectual disposition toward the bigger picture, the longer term, and the cohabitation of many worlds. Therefore, Yun-han declined my offer to debate, on his behalf, with the younger colleagues who challenged his integrity when he expressed reservations about the (pseudo-)liberal democratic appeal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He specifically told me that he did not wish to engage with those “green guards.” In my opinion, however, he was not giving up on them. Rather, he would subtly work on an overall enlightening environment that would only emerge with time. Yun-han had begun publicly to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treating social science as a universal methodology since at leas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10s. Threads of such alienation had been emerging in his syllabi befor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Given over a decade of warming up, he was more than ready to take off after being elected an Academician, a credit that enabled him to move beyo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Other than Marxism, which Yun-han’s early teaching career employed to reveal the cruelty of liberal capitalism, his increasing curiosity about the post-Western thought in the past decade pointed to many of the problematic presumptions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 In fact, he stood at the vanguard of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Western and Chinese studies. His inspiring endeavor is now critically endangered. Sensitive readers who are literate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might sense the alienation of Yun-han’s good-governance work (usually in Chinese) from his Barometer work (mostly in English). Nevertheless, Yun-han incorporated the notion of good governance into some of his English writings, as it is not entirely unfriendly to the political agenda of the Barometer research, which is to spread democracy. In this regard, he enlisted Francis Fukuyama’s reflections on the seeming incapacity of liberalism for good governance to desensitize his purpose of (dis)qualifying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Yun-han took care to reserve his analytical lens of “systemic culture” that he acquired from Professor Hu mainly for his Chinese audience. This concept critically attributes the failing democracy in Taiwan to a culture of systemic cleavages, crafted by the past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I think that he judges that this concept is only ready for those who have already suffered under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historical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In other words, his Anglo-Saxon colleagues based in the former colonizing lands were not yet ready for such a theoretical lens. Unfamiliar with his disposition toward the bigger picture, the assaults on the alleged “China turn” in his more recent Chinese writings were destined to invoke no response from him. After all, Yun-han could not possibly abandon Barometer, which was his home, even if the rise of China gave him a distinct insight into the insufficiency and bias of liberal democracy, now illuminated by a pluriversal light. If Heaven had allowed him a few more years to grow his China scholarship, I feel sure that Barometer would still have a promising future, not only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 in general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but also in the hopelessly involuting liberal West.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at Yun-han’s style of avoiding fruitless rebutting and preparing overall reconciliation for a common future is advertently aimed at believers in both Chinese Socialism and Western liberalism, for the former to understand why the aversion to autocracy in China can result from spontaneity rather than entirely top-down manipulation and the latter to appreciate why the Chinese autocracy cannot help but attend to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instead of simply abusing their power. Without his continuous leadership, however, Yun-han’s drive for mutual learning and unlearning between liberal democracy and Confucian/Socialist autocracy immediately loses steam. I may be overly pessimistic and Yun-han would not want to see pessimism. I may be guilty of projecting my own passion into his bigger picture while Yun-han used to be nuanced and delicate. In any case, I will continue with what I see him leave, in the hope that I might somehow ease the loss of our time. 朱雲漢的愛中國,豈是一個立場? 石之瑜 《朱雲漢教授追思會》上發言節錄版 「全球華人政治學家論壇暨環球兩岸研究會」主辦 2023.2.12 (原版:https://youtu.be/_cMjQjSDk3U) 朱雲漢教授過世,大量親炙過的年輕同仁,爭相為文追思。其中不少人(幾乎如遵循一套公式般)表示,即使與老師對中國的立場迥然不同,更不贊同老師分析中國時,從他早年對民主自由的主張轉向,也仍無礙他們破例懷念老師。
然而,朱教授近十年來豪不忌諱,盡情分析的中國讜論,豈是立場使然?他對中國所處局勢同情理解,無懼詆毀。這樣的坦然令人嫉妒。一妒他高屋建瓴、旁徵博引的理論深度,讓人不敢直視;但更妒他不迴避、不隱藏的自信。 朱教授從數字與趨勢中看到中國的發展,進而推敲其中的文化密碼,是違反民主自由價值嗎?他經歷台灣治理體制的墮落與崩潰,反省民主自由制度難以為繼,不也充滿遺憾嗎?是誰,在對台灣民主的揮霍殆盡,表現濫情的讚賞? 早在民進黨執政之前,朱教授畢生追隨的恩師——胡佛先生——已從中國的治理文化,推敲出台灣民主制度的危機。質言之,一個喪失群體共同性的分裂社會,無法實踐民主自由制度。師生同憂,日後的發展果然如此。 一旦社群失去共同感,則人人擔心受到侵犯,便充滿攻擊性,人人草木皆兵,便吝於互助。朱教授切膚感受胡先生所指出,這時的民主自由淪為鬥爭工具,只用來對想像的敵人制衡,甚至剝奪其權利,卻對自己(人)放縱。 朱教授曾追隨胡先生主張內閣制,正是忌憚總統制造成撕裂效果,會破壞國民相互尊重,刺激統治者及其擁躉,去剝奪政敵的自由權利。這時的民主選舉,是在動員對敵作戰,不是在選政府,無論誰贏,都會製造另一方淪亡的恐懼。 胡先生乃舉文化大革命為例說明,聽命於領袖的紅衛兵,毫未解放,不過是以解放對方為名,遂行敵我鬥爭。同理,台灣的民主自由變成誰有資格當國民的鬥爭。朱教授說的綠衛兵四起,正反映這個群體崩解、民主墮落的時代。 創新繼承胡佛先生的愛中國 胡先生之愛中國,是凜於肉體中國的淪亡危機,為了富強,浸淫西學,畢生致力現代化,鼓吹憲政。但後來發現,台灣殖民歷史摧毀了在地的同群意識。他曾率先引進西學,目睹西學竟一再遭分裂社會濫用,變成壓迫、鬥爭的工具。 痛定思痛的他說,民主化首先是回歸祖國、重建群性的道德問題,故唯有追求統一的台灣,才能重振民主自由。他回憶孫中山對同志的告誡:救中國,不救大清。也就是,超越政權利害,集中心力在群的生存,才能推動現代化。 相形之下,朱教授之愛中國,是在分裂社會的條件下逐漸養成的。對他而言,那是既充滿壓迫,也充滿誘惑;既嚮往西學,也懷疑西學;既屬於中國,也不屬於中國的一種既現實,而又不現實的雙趨矛盾。 適逢全球南方對殖民歷史發動批判,質疑母國事先種下獨立後的族群分裂基因,導致現代化變質,則民主自由充其量是華而不實的海市蜃樓。朱教授在世紀之交就已注意到這股潮流,二十年後更稱之為被「層層節制的自由主義」。 這概念不新鮮,街坊通稱為「鑲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有誰看得懂呢?朱教授別出心裁的翻譯,扭轉了主客尊卑,揭穿自由主義的外來性,更體現出在地社會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世紀更迭前夕,他對西學已然警覺。 奠定朱教授後半生學術志業的,一是胡先生對西學在各地的分裂社會遭濫用後的反省,二是全球南方探索非西方發展路徑的士氣如虹。朱教授猶駕馭中國崛起的教訓,大規模地歸納評比中外治理經驗,賦予中國無遠弗屆的世界性。 在改革開放所實踐的非西方路徑上,朱教授超越了胡先生面對西學的困境;在台灣分裂社會的壓力中,他傳承了胡先生對群性撕裂的診斷;在中國崛起的世界各地之間,他的高思釋放了胡先生對民族淪亡的肉體危機感。 朱教授所愛的,是對分裂社會充滿了政治啟示、對台灣在世界中重新定位提供了戰略啟示、對反思西方現代化道路具備了知識啟示的文化中國。那不是待宰的肉體中國,而是無窮的精神中國;不是危機,是解藥;不是立場,是靈感。 愛護屬於所有人的中國崛起 各界以「立場」描述朱教授的中國敘事,與其說年輕人透過文字,表現自己對老師政治「轉向」的寬容,不如說是藉由對比他們自以為與老師的差異,來凸顯本身的正確立場,表彰自己繼續傳承老師已經放棄的民主自由價值。 按民主自由的價值,凡涉及立場,由各人決定,旁人無由置喙,所以追思時,當然可把朱教授的立場擺一邊。但既然擺一邊,為何幾乎人人不約而同還要畫蛇添足說,我把立場擺一邊?可見,不能擺一邊的,正是表演追思的他們。 此間的追思文章,往往回憶老師的謙謙君子,溫文儒雅,樂於助己。不這樣回憶,如何合理化他們寬恕老師所謂的中國立場?但把他當例外來展示的這條公式,鞏固了分裂社會的敵我想像。而他,決定用崛起的中國呼喚他們猛回頭。 結果,表演追思的人高姿態地寬恕老師,是在掩飾他們對朱教授敲響的警世鐘,惶惶不安——我們不質問老師,那老師對我們的立場也就無權深究。於是,他們自己如何進入現在的立場?動機何在?有多堅定?都逃避不面對。 換言之,若非他們親炙過朱教授,他對中國的立場就不能擺一邊。一旦遭遇不相識的覺醒青年,就得承受尖酸刻薄而不見饒。弔唁者的寬恕因而不是尊重他,影射的其實是對敵霸凌,但饒你一回的立場自白。 此何以胡先生在生前屢次提醒,民主化是道德問題。痛恨自己文化的統治階層,必造成分裂人格與分裂社會,充斥侵略性、投機性、反覆性。認真面對全部自己,無懼於自己,才能對自己言行有責任感,而民主恰恰就是責任政治。 准此,朱教授所歸納分析的中國,不是他個人擁有的中國,而是一整個時代的所有人都擁有的中國。能將自己的所有,加以愛護,不但能養成自由民主的文化基礎,甚至能把受層層節制的自由主義,昇華為文化涵養豐富的自由主義。 ---------------------------------------------------------------------------------------------------------------- (感謝學者王雨舟與郭銘傑提示寫作方向) 朱雲漢教授辭世的消息來得太突然,令人十分震驚與不捨。
我認識雲漢教授,是在1981年。當時他剛進入明尼蘇達大學政治系博士班就讀,我則到該校「韓福瑞公共事務學院」攻讀公共管理碩士學位。雖然我們在不同系所,但我選修了政治系的一門統計課,雲漢也在班上,因此幸運建立起和他同窗的情誼。雲漢在課堂上很喜歡發表意見、與教授互動,我還記得授課教授常稱讚他聰明優秀,說臺灣學生的學識基礎很紮實;而同為來自臺灣的國際學生,我竟也有些與有榮焉的感覺!這是我最早對雲漢的印象。 博士班畢業後,我到紐約州立大學擔任助理教授。雲漢這時也已返回台大任教。1990年,他到美國開會,特地到家裡來看我和外子匡時。那天下午,我們暢談臺灣的民主發展和學術環境,他神采奕奕,滔滔不絕,對學術研究的執著和熱情一覽無遺。而幾個月之後,因緣際會,我也決定收拾行囊回到台灣,成為雲漢教授的同事。 這幾十年來,在同事的眼中,朱雲漢教授是位溫文儒雅的謙謙君子。他一生努力不懈,作育英才,並為提高臺灣學術的國際能見度和影響力投入許多心力,貢獻極大,也留給我們無限的懷念與追思。 雲漢走了,好像天邊璀璨雲彩翩然而去。我覺得此時他想看到的不是大家的驚愕、悲歎與不捨,而是記得他一生的成就與風華。簡單地來說,雲漢是世界級的政治學者,溫柔敦厚的儒士,滿懷家國情懷的知識份子,以及善於品味人生的大師。這四點,缺一不足以描摹雲漢。
雲漢是台大政治系大我三屆的學長,在學校就有才子的名聲。1987年他從明尼蘇達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回母系任教,我四年後繼之,從此我們在政治系做了32年的同事。後來胡佛院士倡議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政治學研究所,先成立籌備處,我們二人乃一起去中研院,為新所打基礎,但仍在台大合聘教書。當時由我擔任籌備處主任,雲漢是所裡敦請的第一位特聘研究員。中研院的這一段,我們又同事了21年。這兩份同事的情誼,如果加起來超過了半世紀,相處時間之長,應該是少有的。 雲漢是世界級的政治學者,毫不為過。他師從胡佛院士,是胡老師的大弟子,從台大組建第一個調查研究團隊時,就參與其中。胡老師的這個計畫,後來擴展到兩岸三地,而且在雲漢回國後,逐步擴展成為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BS),並與世界民主動態調查連繫起來,組成了一個國際性的學術網絡。這是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下從民主價值變遷的角度來進行的一個規模龐大的國際政治學研究計畫,而雲漢承接著胡老師,帶領台灣的學者,在這其中取得了亞洲地區的領導性角色。如此成就在全球華人政治學者當中是空前的。雲漢與亞洲及全球從事民主化相關調研的學者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建立起聯繫網絡,相互支援,並且獲得了國內與國際許多主要研究基金的支持。其規模在台灣的政治學界無疑是最大、也最為持久。 這樣一個重要的國際政治學術組織的建構,是極為艱辛的。ABS除了直接進行一波波的調查研究之外,又指導與支援了多個國家的調研工作,並整合建立了整個區域的資料庫,扮演行政協調的角色。其中各式各樣的討論談判、折衝尊俎,極為勞心費力;而為計畫持續籌募研究資金,更是雲漢直到過世那一天都時時刻刻、心心念念的大事,這對他的病情無容置疑地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雲漢是一位溫柔敦厚的儒士,這一點跟胡佛老師一樣。他們一心嚮慕西學,如五四諸子一樣想用民主與科學來救國,但是其待人處事完全是溫厚的儒家典型。雲漢對學術前輩執禮甚恭,對同儕慷慨大度,對學生則關心照顧、非常溫柔,和他相處過的人絕不可能無感。他才思敏捷但絕不盛氣凌人,執著理念但溫和婉轉,不在同一個文化情境之下的外國學者也樂於和雲漢合作相處。記得一位很資深的美國政治學者前一段時間來台,但是沒有見到雲漢,深感可惜,他在臨行前跟我說“Yun-han is such a sweet person”。我想了一下,瞭解到他這樣說的原因,是雲漢總是熱忱地接待國際學者,並且體貼地為他們的研究需求多方設想。我和雲漢有一些共同的學生,即使在國外教書發展還是持續保持聯絡。這些學生回台灣來的時候一定會來看老師,而我也因此知道雲漢對學生的關照是如何體貼入微。不論是以前還是現在的學生,能被大師鼓勵肯定,是會長久記憶、甚至影響一輩子的。雲漢這樣感動了好多的學生,讓他們走上了學術的志業。 雲漢的儒士之風還可以從另外一角度來看。多年來我從旁觀察,深深感覺到雲漢對胡老師不僅是當成恩師來尊敬,而胡老師對雲漢也不只是當成他的大弟子來培養提攜,他們兩人是情同父子的。胡老師在引進政治學的科學方法以及開啟調查研究的風氣潮流方面是國內第一人,而雲漢則完全繼承了胡老師的理念。在2018年胡老師過世,雲漢為胡老師盡心籌辦了一場追思會,並在會上為臺大社科院的「胡佛東亞民主中心」揭牌,場面非常感人。這當然是為了紀念胡老師開創的功績,也是充滿了雲漢與一整代學術界對胡老師的師慕之情。從這些師生的互動,我看到儒家的風範,也看到中華文化傳統中美好的一面。 雲漢是滿懷家國情懷的知識份子。雖然他的研究多是運用數量工具來進行精細的社會科學分析,但是他的起始點與一貫的初心是高度理想主義的。以前胡老師在教導台大一屆屆學生的時候,總不斷提醒大家要盡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講到「知識份子」這四個字的時候,語調一定特別高昂。我知道那是一項期許、一份使命感,和一種甘盡全力、願意為理念而犧牲的心態表述,展現的是對統治者的一種寧折不彎的骨氣。在這種心情之下,雲漢始則以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為圭臬,並研究在台灣如何進行民主轉型,又如何可以達成民主鞏固,這反映在他前期的專書著作,包括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與《台灣民主轉型的經驗與啟示》當中。到了後期,雲漢觀察到民主體制在實際運作上的種切缺失,乃又不惜與多數意見相抗,坦率地批評西方民主,並指出中國與東方的興起,以及中國模式有其合理性,而後者在台灣是有極大的政治爭議性的。他的《高思在雲》、《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與和鄭永年主編的《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全球新秩序的興起》是這個階段的標誌型著作。雲漢最後一篇公共論述,是在過世前一個月在《天下雜誌》發表的「美國軍售地雷,台灣必須覺醒」,縱身躍入一個爆炸性的議題當中。雲漢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憂國憂時,發抒己見,無論在什麼樣的政治環境,都慷慨陳辭,這份志氣,也是從恩師胡院士那裡一脈相承下來的。不同意雲漢觀點的人,可以和他進行學術辯論,但是不能夠否認他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和油然而發的諤諤之言。 最後,雲漢是善於品味人生的大師。許多與雲漢相識的學術中人,都知道雲漢對生活有藝術性的品味。他是一位美食家,對於東西菜餚、名家餐館如數家珍。他在國際行走,又在對岸走遍大江南北,閱歷豐富,無論品茗、論酒,指點佳餚,勝過專家。去過蔣經國基金會、受過雲漢招待的學者,不可能不驚訝於主人的精緻品味。我最嘆服的,是雲漢以逾十年的努力,百折不回地建構了七海文化園區,創建了蔣經國總統圖書館,其建築的巧妙佈局、色調的層層搭配、雅致的多樣選材、與氣魄的開闊展示,都讓人讚歎不已。在宴會大廳旁的牆上,有一幅胡老師所寫的蘇軾「念奴嬌」,從大江東去寫到一尊還酹江月,氣勢磅礡,筆力萬鈞。這也是雲漢最愛與人介紹的,一來展現出胡院士的名家書法,一來也更讓人感受到雲漢對恩師的敬重與推崇。 一位碩學鴻儒、謙謙君子、憂國學者、品味大師從此仙逝,但是他所遺留的,何其豐富。如何讓他所夙夜經營的能夠長久存留,持續發揮影響,而不至人走茶涼,會是懷念雲漢的人所該心心念念、不能遺忘的。 雲漢兄是我大學時期就很敬佩的學長,我回台灣任教後,他也時常邀我參加一些國內外的學術研討會,後來他還曾經把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的棒子交到我手上,我很感謝他的提攜與照顧。
雲漢兄是具有高度國際知名度的台灣政治學者,對於國際和兩岸的學術界都有重要的影響力,這些年來他奔波於各種國際學術場合實在是太辛苦了。 對於他的提早離去,我感到非常的震驚、不捨與難過。祝福雲漢兄一路好走! 2021年1月28日,朱老師抱恙出席歐盟代表在官邸為我舉辦的新書發表會,讓我感動難忘。
那是我最後一次與朱老師交談、向他當面請益。 朱老師驟然辭世,讓台大、台灣、整個中文圈,頓失一位傑出的政治學者、歷史學者、思想家、教育家和諤諤國士。 向朱老師致敬,也緬懷他的教導、述論和風範。 蘇宏達敬輓 朱雲漢教授的仙逝,是國內乃至國際政治學界的憾事。過去多年來,我除了作為學術界的後進,得以管窺受益於朱教授的恢弘學養之外,特別感念於心的,大抵有三事。一則是擔任系主任期間,他曾數次主動提及邀請美國重要政治學者前來系上講學,並協助建立聯繫。他這份對於系上持續的關懷和支持,無疑是為本系帶來精進提升的重要動力之一。二則是我承乏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期間,他對於會務的關注叮嚀,以及實際協助。三則是趙副校長永茂,在追思感言中提到的,透過朱教授的牽線推動,在我協助趙副校長推動社科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學術活動期間,從2012年起,與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以及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共同主辦兩岸青年學者參與的暑期社會科學高級研習營。我還記得在最重要的一次籌備商談中,他和當時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鄧正來院長,與大家一起思考討論了三個多小時,最後定案,為後來研習營的穩定推動,奠下關鍵性基礎。而研習營本身,也同樣得益於他作為蔣經國基金會的執行長,所挹注的基金會資源。事實上,數年當中,每次前往基金會進行研習營推動成果報告時,都會遇到頗多由國內其他領域(例如歷史領域、史語領域、社會學領域等)共同和中國大陸相關學術機構舉辦類似活動的先進,他們也同樣受到基金會的積極支持,促進兩岸青年學者間的交流互動。我相信,這些在著書立說之外所帶來的貢獻和影響,也具有同樣重要的典型在夙昔之意義。
2023年2月5日晚上9點多,我接到老師過世的消息。當時腦筋一片空白,如同作夢一般很不真實。老師生病五年多,癌細胞一直控制得很好,過年期間我們還互傳賀年簡訊,我根本沒想到老師走得這麼快。
1987年老師拿到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後,放棄芝加哥大學教書機會,收拾行囊回臺大政治系。剛開始老師和我接觸不多,我們在胡佛院士領導的調查計畫一起工作。老師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厲害,橫跨多個政治學次領域,不論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比較政治,甚至深奧難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過去或現在,臺灣政治學界幾乎沒有出現過老師這樣的人。 1993年我退伍後,陷入人生重大抉擇,到底要就業或出國唸書?老師遞給我第三條路。有天晚上老師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考上博士班了,以後就跟著他,其他的事不用想了。老師做什麼,我就做什麼,老師有多忙,我就有多忙,師生情誼一晃就要滿30年。1995年老師在臺灣舉辦「第三波民主化」國際研討會,這場會議中邀請很多位國際最知名的比較民主化學者蒞臨,會後出版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rends and Challenges,這本書後來成為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經點書籍之一,奠定老師後來成為民主化研究領域中國際學術領導的地位。 老師一手創立與推動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計畫,是一項偉大的成就,把台灣政治學的研究成果推向國際化。自2004年以後,本計畫正式成為「民主研究機構網路」(Network of Democracy Research Institutes, NDRI)的會員,此網絡為全球性學術組織。並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UNESCO)評定本計畫是全球重要大型調查資料計畫之一,同時獲得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奧斯陸治理中心(UNDP Oslo Governance Centre)的認同,列入該中心收錄之全球良好治理指標中。在Russell J. Dalton,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以及Carles Boix, Susan Carol Stoke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這兩本政治學最重要的參考工具書裡,均將本計畫列為全球政治學重要大型調查研究計畫之一。同時,「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也讓臺灣政治學者,經常在有影響力的國際期刊,發表全球民主發展的趨勢及問題。 跟老師相處越久,越感受到與老師之間的差距,只能說老師具有超凡能力,我們這種平凡的人永遠追不上。幸運的是,老師都會停下腳步拉我們一把。臺灣學術界受惠於老師教導與提攜的後輩很多,我們這群人永遠感念老師。老師臨走前,最後一次和我通電話,特別交代我要好好協助把「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繼續推動下去。這是一個很艱難的任務,我會盡我全力推動下去。請老師一路好走,放下的重擔由我們承擔,會一棒棒延續下去。 記得第一次上朱老師的課,已經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事情。那時候興起報考政治學研究所的念頭,選了幾門政治系的重量級課程,其中一門便是朱老師和高朗老師合開的比較政府。老師介紹英法政府體制,談及致力改造英國工黨的黨魁金諾契和備戰總統大選的巴黎市長席哈克,把人物個性和體制特色結合得惟妙惟肖,讓我更加渴望探索政治學的堂奧之美。 進入台大政治學研究所後的迎新活動,介紹朱老師時特別談到他品鑑紅酒的造詣,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朱老師在飲食文化上的講究,霎時間一幅認真治學者的夢想生活映入眼簾。多年後回到母系任教,因為陪朱老師一起接待國際學者,也有幸跟著到台北一些知名餐廳大開眼界。除了佳餚珍饈讓人大快朵頤外,額外的收穫是見證朱老師絕佳的英文功夫,不只各樣佳餚和所用材料的英文名字可以輕鬆的信手捻來,就連烹飪做法和不同做法間色香味的差異,一樣可以用英文娓娓道來。每次晚宴後,我都懷疑自己是不是學過英文,也考慮過該不該去報英語補習班進修。 當然,朱老師的治學途徑和背後深刻的哲學觀,深刻影響我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寫作。我剛回母校任教時,因為朱老師大方邀請我和他一起開課,為我開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旅程。眾所周知,朱老師長年耕耘調查方法研究政治文化,我本以為朱老師會專注於實證主義典範的開放經濟政治學。等開課後我才知道,他更重視和葛蘭西、阿瑞奇等馬克思學派間的對話,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的收入不均和欲振乏力批判的鞭辟入裡,他是在掌握科學方法的基礎上勇敢的面對科學方法的不足。 毫不誇張地說,2008年金融海嘯前我們頭一次並肩授課時,朱老師對馬克思學派的認真對待讓我受到不小的震撼。然而,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大師Benjamin Cohen在2019年出版的理論書也承認,多數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都有相當的馬克思學派傳統,開放經濟政治學以國別來說反而是少數。因為跟著朱老師一起上課,我不但重新上了好幾回國際政治經濟學,還能夠從理論高度欣賞和學習馬克思學派,這是博士班畢業後最扎實的再啟蒙教育。 正如他在科學方法的基礎上挑戰科學方法,朱老師同樣在瞭解西方的基礎上反思西方發展路徑的不足。疫情前,朱老師大致每個月都會有國際旅行,他的學界好友遍及五大洲,並充分掌握國際學術界的最新辯論,也以此開展對於西方極化政治和財富不均的反省。朱老師常勉勵後進努力做公共知識份子,他也在無數的專欄文章中展現他對知識份子社會責任的承擔。當然,參與公共政策的辯論不免被社會標籤,但我相信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觀念和嚴謹的西方學術訓練已為朱老師打造強大的內心世界,這些足以勝過世俗的偏見,而且得勝有餘。 去年八月我撰寫的教科書問世後,我寫信問朱老師的近況,他回信後我再去信表示想帶著教科書去看他,但他沒有回覆,只好拜託基金會的同仁把書送去,不想這竟是我們最後一次書信往返。 二月六日清晨知道朱老師辭世的消息,我腦中湧現出是五年前胡佛老師去世時朱老師主持紀念會的場景。在紀念會上,除了看到朱老師藏在他矜持外表下的真情至性外,還有胡老師留下來的一句斗大的提醒「民主、科學、愛中國」。 也許「中國」這個概念在很多人感覺已經不合時宜,但在我看來,那不只是家國情懷,還有著對美好未來的追求,追求一個「充滿公平正義」,「永遠有對人道、人心、和人本質的尊重」的理想國度。這樣的家國情懷,不帶著強迫,不讓人為難,可以和不同的歷史感情並肩,又能不斷激勵人心。這是胡老師那個世代的執著,也是朱老師那個世代的承擔,希望有一天在我們這個世代,以及我們之後的世代,還能看到這樣的傳承。 老師,謝謝您為我開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旅程,謝謝您為我們創造一個知識份子的完美典範。很遺憾沒能當面感謝您,沒能向您好好道別,僅能以此短文表達我無法道盡的感謝,也相信您已離苦得樂,在另一個世界享受上好的福份。 正東敬悼 Click here to edit.
2/15/2023 從1997年夏天老師答應當我碩論指導教授開始,至今我追隨朱老師已經26年了。絕大多數當我們意見相左的時候,老師一次一次都用他神準的判斷讓我感到自嘆弗如;但是一月中的這次,儘管我極力隱藏不說,恐怕是我的預感比較準確。然而從過去十天與老師各方親友的往來資訊得知,看來我並沒有比老師更清楚他的健康狀態,事實上他追求的是一種極致淡定的境界,一個他過去26年來教導我要學會的處世原則。 在1月9日晚上8點9分,老師突然通知我隔天要開緊急會議,我下意識問是要視訊嗎?老師意外的說不用開鏡頭吧!1月10日中午開會,老師交代了今年6月ABS和GBS的會議安排,並且囑咐我千萬不能搞砸,要負起責任。接下來在1月11日下午1點52分、5點58分、9點24分,連續打了三通電話跟我點出一些聯繫工作上不夠細膩的問題。而在休息一天後,在1月13日下午1點31分、2點29分、2點42分、6點16到42分連續四通(因為邊停車通訊不好)、晚上11點30分、11點34分(未接起)又撥了電話,都是在交代許多日後ABS和GBS團隊合作和未來發展的細節事務,讓我感到十分惶恐,因為這些事情都相當瑣碎,應該沒有時間上的壓力。最後在1月14日,那天我帶黃小妹去台南參加碩士指導學生婚禮的晚上,在煙波大飯店又接到老師在9點34分(未接起)、9點45分(我回撥)、10點49分的電話叮囑如何跟GBS各區域團隊和其他相關國際學術計畫交往的事宜。 從1月11到14日,我在其中三天一共與老師有15通手機通話的往來,這大概是我過去十年間的總和,我的腦海在那時瞬間產生巨大的疑惑,老師怎麼了?儘管我有不祥的預感,但私下詢問,老師一切如常。儘管還是有經費變動上的事宜,但我只能怪自己多心了,也慶幸自己的預感是錯的。 直到2月4日中午,傳來老師意識不清,一直昏睡的消息,經過詢問其他經歷類似經驗的朋友,得知這是很正常的情況,離最糟狀況多半還有數個月。但在隔日晚上九點多,就聽到老師仙逝的噩耗。我的預感是對的,而老師事實上已經做了他心裡認為的適當安排,這15通電話的內容是我承繼師業的中心準則,並且這是我見過他第一次最不淡定的狀況。看來一切要怪我,因為我一向有緊張的毛病,做事情不夠牢靠,讓老師操心了。 其實老師在年前就已經在裝修上做了安排,這反映老師早有跟我一樣的預感,但是他的淡定,極致的淡定,讓身邊所有人都無法察覺他早已了然。但這樣一個完美離開的計畫,卻因為我的能力不足令人擔心,而讓老師不得不焦急的要我正視他的交代,因而我油然而生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如果我夠淡定,如果我真的學習到老師26年來的教誨,我應該在第一時間明瞭老師的用心,以接受考驗的嚴肅態度跟老師應對,讓老師覺得我真的學會淡定,這樣就不至於讓他甘冒失去淡定也要喚醒我的認真。 祝老師在天上得享清福,我會畢生追求老師的淡定教導! 旻華追悼 這是2008年3月4日我和朱老師接待T. J. Pempel (UC-Berkeley)的晚餐照片,當時Pempel是EAI訪問學者,我是系上接待人,當時是我第一次受聘台大,時任助理教授。
這篇回憶的小文起筆的時候,距離朱雲漢老師離開臺大政治學系已有三週。三週以來,許多師友同仁已經寫了不少令人動容的緬懷和推崇其學術成就的文章。後學忝為朱老師的後輩系友與同事,因緣和專業的關係,直接追隨他的機會不多。所以有關朱老師身為國際學術領袖的成就,筆者委實沒有資格贅言。
不過在大學部就讀時,筆者雖因單雙號分班,錯過了他剛返系開授的兩門大課:「比較政府」和「政治學方法論」,只從會議和同學共筆中對他有初步印象。但緣分奇妙之處是,碩士班以後從國關理論觸及科學哲學問題,加深了對朱老師治學思路的親切感。而這些吉光片羽的印象,到自己也回系工作,特別是聆聽他分析國際政經大勢的演講,與拜讀甚至寫作引用他相關著作時,才慢慢變得完整鮮明,也體會到為什麼朱老師不只是一個院士級的飽學之士,更是有魅力的學術領袖。 朱雲漢老師早在1973年就結緣政治學系國關組。1977年又考取母系碩士班時,拜入胡佛教授門下,兩人同為臺灣經驗政治研究方法與民主化研究的先驅。10年之後朱老師從美國取得博士學位返系任教,與胡老師先後當選院士,傳為美談。到今年朱老師在教席崗位上辭世,任教母系超過35年。如果加上在校就讀的時光,朱老師與政治學系相互提攜之情超過40年。朱老師在系時曾開授的「比較政府」、「政治學方法論」、「國際政治經濟學專題」都是熱門精彩的大課。他執教三十餘年,在系上指導超過25位碩博士。若加上在國發所、政大、中山、師大的受業學生更超過30人。這些學生有許多日後成為學科的擔綱者;若說他對政治學系是終身貢獻、鞠躬盡瘁,當不為過。 筆者得以有更多機會體會朱老師的學問和風度,則得益於他傳承和推動胡老師創辦中流基金會的中國大陸交流與研究。淺見以為,這不僅是朱老師為胡老師的遺志繼續奉獻,更與他在政治學系一路以來的研究主題—選舉與政黨、民主價值與民主化的經驗研究、比較東亞 / 世界政治文化與價值、民主品質與治理模式興衰、文化價值對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和變遷的根本性作用,密切相關。中國大陸政經發展與美中大國競爭的劇烈變化,正好是躬逢且注定身陷兩岸危、機交織的臺灣政治學者,必須用溫情與正直去應對的。而其結局與解局,不僅關涉你我和千千萬萬世人的生死命運,也直指危機中現代社會科學的前途。 朱雲漢老師的高思不只停雲在星河之際,也遠遠超越了楚漢相爭的兩極故事,卻似乎永遠定格在2023這個世局大變的前夕。筆者可以確定的是,政治學系的師生會永遠懷念朱老師開朗的笑容。也盼望他遼闊的視野,能給我們帶來祝福和幸運。 112年2月23日 「朱老師是在我大二那年回母系任教的,有幸可以修到他一開始教書開的「比較政府」與「政治學方法論」(後來的「社科方」)。在那個時代巨輪正在轉向的1980年代,不知是因為他的學問還是翩翩風采,當時感覺街頭可以學到比教室更多而成績不大好的我總是會去上他的課,也在這兩科得到較好的成績,但在政研所那一年正好朱老師去哥大客座而沒有修到他的課,然後在紐約與他擦肩而過。
感謝朱老師在我年輕的時候讓我見識到政治學的美好、學者的優雅,並為我寫推薦信,引領我走上政治學者這個生涯道路!雖然近年因為我的女兒生病,他也生病,我已經好久沒有遇到他,聽聞他的健康狀況時好時壞,但消息傳來仍對他的英年早逝感震驚不捨,願上帝保守朱老師得安息,遺族得安慰!」 悼念恩師:朱雲漢老師
雖然知道朱老師已經病了幾年,也聽聞他近來身子狀況不太好,但老師驟然離世,還是令我們非常震驚、難過與不捨。 朱老師當年的政治學方法論課程開啟我對學術研究的興趣,時至今日仍難忘懷老師當年上課的風采和精闢內容。進入台大政研所就讀後,有幸在研一開學前的暑假,便加入胡佛老師研究室(又稱306研究室),擔任胡老師和朱老師多年的研究助理,受到老師們許多的指導和照顧。往事歷歷在目,其中有兩件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不曾或忘。第一件事,是胡老師曾私下和學生們說,哪有人什麼都懂,什麼都能發表意見呢。在那之後,我了解到,學者應該在自己真正專精的領域發言以及發揮影響力,而且務必慎重為之。另一件事,是朱老師非常重視調查資料的正確性。他曾說,若資料的品質無法確保,會讓他難以安眠,他希望我們在輸入和檢查資料時(這是我當時在306研究室所負責的工作),要多加用心。這讓我了解到,研究的每個環節都必須非常嚴謹,資料的正確無誤是重中之重。 雖然我後來也曾寫過關於政治態度和行為的文章,但因為我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政府體制等制度研究,所以和朱老師在學術上的交集並不多。不過,朱老師一直待我很親切,在我人生許多重要階段給予幫助、鼓勵、肯定和提攜。我始終記得朱老師當年對我碩論的讚美,他是我的論文口試委員,在口試時,朱老師說我的論文寫得很好,應該沒有什麼好問的。口試當時我很緊張,也沒有想過能夠得到朱老師如此高的肯定,而這對於當年想要出國繼續深造的我來說,有莫大的激勵作用,也是我畢生引以為傲的事情。 跟在朱老師身邊學習和工作是幸福的。除了許多他的學生都曾提及的(而我也都曾受惠),朱老師常常請學生吃美食,和學生解說美食,甚至邀學生到家中作客,並用心幫學生寫一封又一封的推薦信,協助學生申請到理想學校,更重要的是,朱老師會提供很多難得的機會,放手讓學生嘗試,從中學習,進而成長茁壯。朱老師相信學生,他願意給予機會,也不擔心學生搞砸,他知道學生會盡力完成任務,萬一學生失敗或犯錯,朱老師也從不苛責,而是讓學生從中吸取經驗和養分,得到成長。自朱老師離世後,有些學長和學妹都發文提到了一些相關的往事,大家都十分感念和感謝朱老師當年在自己不小心犯錯時,所給予的寬容和溫暖,以及朱老師一直以來對大家的提攜。 記得在親恩赴密西根大學就讀後,我在原本負責的工作事項外,另外再接手他的助理工作,為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Larry Diamond教授安排政治人物專訪的事宜。雖然對於自政大新聞學系畢業的我而言,這項工作是能勝任的,但當時我還是感到有些緊張,所幸在全力以赴之下,所有工作都進展順利,Diamond教授當時還誇我非常聰明,幫他的專訪行程安排地十分得宜,緊湊且有效率。在306研究室工作,很多時候都有類似的機會和場合,讓我們能參與各種國際交流,認識各國學者。而為Diamond教授短暫工作的經驗,因為得到他的肯定與讚美,也讓我對自己赴美留學一事,更添自信與對自我的期勉。多年之後,我以學者身分,參與過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所舉辦的幾次研討會,同樣有許多收穫。如今回想起來,除了感恩朱老師一直以來對我們的照顧,更遺憾自己沒能投入更多相關的研究,與朱老師有更多學術上的合作與交流。 於學術外,朱老師也多次溫暖地照拂我們全家。在親恩和我的婚宴上,朱老師擔任我們的證婚人,上台為我們的愛情見證祝賀。婚宴結束後,朱老師將賀詞稍加修飾,寄予我們留念:美鳳于歸,如玉珍惜,朝夕親吻,終生恩愛。感恩朱老師的照顧,感恩老師們的306研究室,讓我尋得人生中的佳偶。再過幾年,親恩和我有了寶寶,購置房產,一次在學術場合與朱老師相遇,朱老師開心地恭喜我們,說我們五子登科,人生圓滿,他很為我們高興。數年後,我們的孩子長大了,可以接受長程旅行,於是幾年前在澳洲開會時,我們把孩子一起帶去。朱老師和宇珩並沒有直接對到話,但朱老師從旁留意觀察宇珩的言行舉止,然後對我豎起大姆指,誇獎我把宇珩教得很好。老師的讚美真是讓我瞬間又開心又感動。常言道為母則強,但我有許多時候其實覺得為母不易,因此,能得到老師對我身兼母職的肯定,著實是很大的鼓舞。朱老師總是像這樣,細膩又不著痕跡地,在我人生各個重要階段和面向,給予關懷、肯定和祝福,我也會帶著這些珍寶般的回憶,繼續努力扮演好我人生中每個角色。 朱老師的優點無法道盡。我們知道他律己甚嚴,每天每個時刻該做什麼,他都按表操課。他曾自剖,自己有一個很好的特質,就是他極具好奇心,對各種新知、新的國際局勢變化和社會脈動,他都會去了解,然後永遠在準備學術旅行。他又具有全方位智慧。因為調查工作很辛苦,有時候徵才並不容易,但記得朱老師曾說,他並不擔心徵不到人,也無需勉強想離開的人,因為一定會有有興趣的新血不斷投入。是啊,在我自己後來也成為學者,才明白朱老師的話真有道理。而最最令人感到佩服的,也是許多學術先進所提到的,是朱老師的家國情懷,是朱老師對台灣的民主、處境和兩岸關係的擔憂,以及對世界局勢發展的關懷。2014年因為服貿協議的簽訂,引發很多爭議,朱老師在天下雜誌撰寫文章,標題是:「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當時我在臉書分享自己的擔憂和看法,也分享了朱老師的文章連結。記得當時我因為很焦慮,曾寫信給朱老師,希望他能多站出來說話,讓更多人了解這個議題,從而化解爭議。但談何容易?胡老師實為先知,他很早就已指出,台灣在國家認同上的分裂一天不解,許多問題只會愈來愈嚴重,民主自由也無法真正落實。朱老師必然也了解這點。我記得朱老師當時應該沒有回覆我的信件,如今回想,自己是太天真了,而且朱老師有自己的節奏和規畫,雖然他後來的諸多著作仍然在社會各界引來許多批判和誤解。 但又何妨?老師一直是寬容、具有海納百川胸襟的人。他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熱愛,對民主自由理念的信仰,無庸置疑。他從不論人是非,道人長短,是零缺點的謙謙君子。他的學識淵博,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享譽兩岸和國際。他不計個人毁謗,言所當言,無所畏懼。他極具品味,為人內斂優雅。他的身教言教,所帶來的影響,以及一切的一切,都將珍藏在我們的心中。 想念恩師,感謝恩師,難捨恩師。願您一路好走。 鳳玉敬悼 2023年3月1日 ”旅次期間得知老師仙逝,聞之實難以置信。從學生時期到進入學界服務的這數十年間,有機會在諸多不同場合親炙老師的治學與處事之道,並共同著述,陪同造訪世界各地,此間收穫實難以勝數。師恩難報萬一,只期往後學生能不負期待,在學術道路上延續與發揚老師留下的良好學風。永遠感懷老師的學者風範。“
與其他同儕相較,我和朱老師的關係比較特別,因為我既非老師的學生,也非台大畢業生,若非因緣際會,朱老師對我而言可能只是一位相當知名的政治學者,如大眾般透過電視與報章雜誌吸收他對國際局勢的看法。但非常幸運的,在一次巧遇中認識朱老師及其團隊,從此開啟我的學術生涯。朱老師對我而言不僅是導師,同時也是伯樂。 在泰國遇見伯樂 2004年我剛結束在瑞典的碩士學程,經友人介紹至泰國的學術機構工作,恰巧該機構是朱老師主持的亞洲民主調查的泰國調查合作團隊。該年朱老師率領台灣團隊成員至泰國曼谷開會,母語為中文的我自然被泰國同事推出來做為聯絡人。猶記在下榻飯店接待台灣團隊時,朱老師相當驚訝我的中文能力,在得知我其實是台灣人後又相當好奇為何我會至泰國工作。那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國際會議邀請了各國調查團隊,會中我成為主要接待,幫忙泰國同事翻譯並解決會中的大小溝通問題。記得在台灣團隊離開的前一晚,團隊成員把我叫到旁邊,問我是否有意願回台工作,後來得知是朱老師想挖角我至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當時還是計畫)擔任專任助理。現在想來真是感謝朱老師慧眼識英雄,雖然當時的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婉拒了,但一年後當我想回台工作並連絡東亞團隊時,朱老師二話不說的應允,開啟了我學術生涯的第一步。爾後擔任專任助理的三年,我一邊從事行政工作,一邊也學習調查與統計等與計畫研究相關的知識。
朱老師立言立行,對我而言是伯樂,是導師,同時也是如父般的存在。朱老師已遠離卻沒有真實的感受,我想是因為他的影響已成為我立身處世的一部分。唯一難過的是,無緣繼續感受學習這份深遠的影響。然緣起緣滅,願朱老師留下的legacy永存人間。
黃凱苹 2023年2月18日 「在對於政治學還懵懵懂懂的時候,有幸修習了朱雲漢老師開設的《社會科學方法論》,還記得是在以前法學院的大禮堂,整個政治系二年級三個組的同學齊聚一堂,寬敞的大禮堂內飄散著各種味道--汗臭或食物香,夾雜著各種聲音,有嬉鬧聲、低語聲。接著,在偌大的舞台上,出現了一個風度翩翩、自帶氣場的老師,總是微笑著開始講課,不多一句寒暄,就開始闡述「科學」和「典範」的發展歷程,不時帶著身為知識分子對於「科學」的自嘲。內容其實略帶艱深,但老師總是微笑著帶領我們進入一個又一個科學發展背後的邏輯,從這堂課開始,對於這個世界的知識、對於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突然有一種撥雲見霧的清朗。即便到現在,朱老師在大禮堂的黑板上畫了一個個典範理論如何被修正、補充或挑戰的板書,仍歷歷在目,這就是老師清楚且有力的講課風格。雖然在進入政治系服務後,未能直接表達對老師授課功力的敬仰,但是,每次和老師見面都會忍不住流露敬佩眼神,我想老師是知道的。朱老師,真的很感謝您,也很幸運能夠修過您所開設的課。 」
小娟 那年申請學校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向朱老師提出撰寫推薦信的不情之請。朱老師爽快答應,親筆寫了十四封的推薦信。二月初,與朱老師分享來自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第二個錄取通知時,朱老師回覆寫道:
我相信你還會拿到更多更好的。記得一旦決定去哪裡,要趕快通知不去的學校,讓候補的補上。雲漢 雖然是小小的叮囑,但卻反映朱老師此生為人一貫滿滿的敦厚、周到與細膩。 申請學校的事塵埃落定後,朱老師邀請我擔任他的專任研究助理,負責籌辦一個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朱老師對助理的完全信任與充分授權,不但讓自己有意想不到的空間可以發揮各種創意來籌辦會議,同時也得以有幸首次見識到朱老師在晚宴上與眾多外國學者談笑風生的博學多聞與風趣高雅。 雖然只是短短四個月,但卻對朱老師有更深層的認識:朱老師不但是一位享譽國際的政治學者,還是一位廣結善緣的學術企業家。 學成歸國、返台服務後,我與朱老師有了更頻繁與密切的學術合作。朱老師請我一同協助劉兆玄院長進行「王道永續發展指標」的設計與建構;朱老師請我負責籌辦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Gary King先生首次來台訪學的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朱老師請我陪同前聯合國安理會主席Kishore Mahbubani賢伉儷到中台灣參訪;朱老師也請我協助他與鄭永年教授合編《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全球新秩序的興起》一書的英文版與中文翻譯版;朱老師還請我與他和黃旻華老師共同發表他此生的最後一篇英文學術期刊論文;朱老師甚至邀我與他和左正東老師在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共同開授「國際政治經濟學專題」,直到辭世的最後一學期。 當年如果沒有朱老師的推薦信,也就沒有今日之我。對朱老師的提攜之恩,只有由衷和溢於言表的感謝。 謝謝朱老師讓我在而立之年就有許多機會在這個多元而立體的世界中大開眼界。不論是在台北圓山飯店國宴廳成為座上賓,還是去澳大利亞雪梨Tamarama海岸秘境目睹太平洋的浩瀚;抑或是到印度Bangalore感受牛與車在路上同行的另類現代性,還是去貴州親歷黃果樹瀑布、千戶苗寨與天眼的碩大之美;甚至是體驗直接搭車從西華門進入北京故宮博物院內的瞬間心理震撼。雖然看到得很多,但受限於篇幅而能寫得實在太少。 朱老師如今已羽化成仙。未來雖然不敢奢望自己成為和老師一樣享譽國際的學術企業家,但自許至少能在待人接物上像老師一樣敦厚、周到、細膩,還有不遺餘力地提攜後進。至於朱老師優雅的學術品味與生活美學,則將在潛移默化中長存我心,並在老師執教長達36年的母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繼續傳承下去。 銘傑敬悼 於2023年3月4日告別式後 各位師長同仁大家晚安。
相信大家今天已經獲知我們敬愛的同仁朱雲漢老師,不幸於2月5日夜與世長辭的消息。本系於6日凌晨得知後,也已於上午9時在系網公告。全網訊息本週亦調整為單色呈現,表達師生與系友無以言表的哀思。感謝系辦同仁凌晨至今協助辦理各項事宜。 方才經玉山老師、佑宗老師分別賜告蔣經國基金會方面關於弔唁時間地點的訊息,並囑託轉達。 朱老師處世儒雅淵博,治學嚴謹活潑,桃李滿門,又關心家國與世界的命運和前景。他是系上教學研究的典範,也是國際學界推崇的學術楷模。他突然離開,不僅是本系的不幸,也是全體政治學界的巨大損失。 盼望大家緬懷他的風範時,也保重身體。願朱老師的精神,永遠與我們同在。 沉痛悼念朱雲漢老師! 系主任 張登及敬上 112年2月7日23時 |